日期:2023/07/20 17:01作者:佚名人气:
胡兴法:大牛圈第一节牛圈猪圈短篇小说
第658期
大牛圈 短篇小说
作者/胡兴法
大牛圈
第一节
牛圈猪圈,也是父亲心血来潮,瞅哪舒服,哪顺眼,就在哪找石头砌上。只要不隔人住的几间屋太远。单门独户的,人和牲口,得相互照应。人照护牲口吃喝,牲口照护人力气、营养、还有那些温顺的脾气。
父亲主持砌了一个大牛圈。后来我长大,腿跑遍村子,才发现其实是全作坊村最大的一个牛圈。
大牛圈在稻场下方。总不能让牛羊住我们上方,占了上风口,让我们白天饿了,听它们磨牙回嚼,夜晚睡了,听它们梦话声声。这个问题父亲早考虑到了。
大牛圈足有我们住的二间屋大(那时还没有接上第三间房)。在这点上,父亲让牛的圈和人的屋第一次划上等号。村里,哪家能摆开这样一个等号呢。
是的,牛圈一定要足够大。我放过多年的牛。我看懂了它。牲口中,它们个子最大;它们看似慢吞吞,其实最喜欢酣畅的呼吸;没事时,最喜做发情时那种无边无际奔跑的梦。
这些,没个大圈,行吗。
早年间,我们住原来的老屋。老屋是一座破庙,父亲花一百块钱买下的,立在朝阳观这块虎地的虎头上。
牛圈呢,只能将就了。就着庙屋的一堵墙,再打了一堵,两头加上木棒订的柴门,就成了。牛圈只有一摆宽。太窄了。窄得牛不能转过身。
一次夜里,牛转身时,被卡在了圈里,整头牛卡成了个弯曲的秤钩。牛急了,角别在墙上,喘着粗气,吐着白沫。父亲也急了,他在手板心吐了口唾沫,迎上去,用尽全身的劲儿扳正牛角,打开门,像倒车样把牛倒了出去。
那时日子过得多难。父亲没本事砌一个大点的牛圈。砌了也要挨人的斗--到处都是红得像牛眼的人。
将就着,父亲只能像牛一样忍辱负重。
第二节
最多的时候,大牛圈关上了三头牛、五只羊、二头猪。多热闹宽敞的一个家。牛可以爬跨调情;羊可以摇着胡子站在石包上装老学究;猪要么叽叽歪歪,要么把梦做到了它的前生今世。它们之间相处很好,不打架,不搞种族歧视。
几十步外的稻场坎上,就是我们这个热闹家庭。父亲、母亲、大哥、二哥、我、妹妹。当然,还有几十只鸡、一大一小两只猫、一条狗、墙洞眼儿里的一窝麻雀。
有这样两个家,不,是一个共同的家,我们过得热闹。少年之前,我从没感到孤独。当朝阳观的第一把阳光像种子样撒在我床头上时,也撒在了牵出大牛圈门口的牛身上。
一大早,开始放牛了。牛牵在人手里,牛看什么时,也学着人的样,眯起眼,很享受的样子。
大牛圈的墙,是用石头砌的。上面盖的是茅草。
砌牛圈,得用很多石头。除就地取材外,不足部分,父亲从远处一个个背来。这得流多少汗,费多少劲。他下了很大决心。他想让这个牛圈沿用下去,直到很长时间。
五年,还是六年,这个村子最大的牛圈就废弃了。
想废弃一个牛圈太容易了。三场雨就可淋透屋顶,五场风就可掀开圈门,七千只白蚁就可凿断中梁。基脚的石头可以自行散场,向来路返回。每个石头都记得自己的来路,与人一样。
父亲最清楚,废弃一个牛圈比砌好一个牛圈容易。何况这个最大的牛圈。他也想挽留住,就像留他的石匠师父多住几天。
可后来连续发生了一些事。关在大牛圈里的一头黄牛摔死了。一只羊得了原地转圈的怪病。猪也相继死了几头,都是长到上百斤的猪。
母亲开始埋怨父亲。
"仗着地儿宽,看哪顺眼就哪儿砌,这回可好。"
"还给别人看人住的屋场地儿,自家一个牛圈地儿就相不好。"
"不会看地儿的就知道,这牛圈地明显阴着嘛。"
村子里,好多房子的风水是父亲看的。好多老人最后一间房子的地儿,还是父亲看的。
大牛圈在我们几间屋的稻场下方,是个凹槽,确实阴着了。这是事实,不怪母亲埋怨。
据村里老人讲,我们住的朝阳观是块虎地。地形嘛,是一头虎的轮廓:虎头是朝阳观山顶的庙屋地儿,虎腰就是砌大牛圈的地方,虎屁股是我们两间屋的小山包。
父亲不敢对着干了。他不是怕母亲,是怕母亲的这句话。
"阴着了",说到点子上去了。
每天,朝阳观的日头刚好从虎头升起,像娃娃醒后的一张脸。虎头把阳光一挡,就轮不上虎腰了。大牛圈找不到白天的出口,套在一个黑口袋里,四处乱撞。这是多绝望的焦急。它把这份焦急分摊给了关在里面的牛、羊、猪;转嫁给了牛圈里的一窝老鼠、一群蚊子、一户蚂蚁。傍晚,太阳从状如虎屁股的小山包落下去时,像个老人的脸。我们的二间房、晒粮食的稻场又挡住了仅有的光,阴住了它。
一件东西一旦阴住,阴到了时间的暗流中,摸索向前摆渡,它就完了。
要是从娃娃到少年,我在朝阳观的日子里,不被每晚的黑暗阴住,我想,我会永远活下去,顺着一条明亮的河床飘下去。
时间这条河,没个尽头。
第三节
那天,那头黄牛刚刚拉完了磨,母亲把它拴在庙屋前的一小块地里。虎屁股上的几间房建好后,庙屋改成了磨房。地窄得像块席子,草却丰茂得像床蓑衣。干了这么多活儿,它累了。母亲心疼它,没把它直接关到大牛圈里,想让它就地饱吃一顿。村里好多人家合伙养一头牛,干完活就直接往牛圈一关,也不管它饿不饿,累不累。大家伙的嘛,你不疼我也不疼。
母亲拴好它后,转身回庙屋收拾磨好的粮食去了。
刚刚下了几天雨,地松松的,软软的。饱胀的墒情,像发酵的麦面粑粑,像母牛喂奶期的奶包。突然,黄牛一脚踩下去,踩到了培坎边缘,前蹄向下陷落。这感觉,类似我经常做的一种下沉的梦。这种下沉没个底。要说有的话,底就是虚无。黄牛感觉不对劲儿,慌忙抽出前蹄,转回身子,准备逃离。身子转回来了,两只后腿却拖了后腿,陷了进去,整个身子重心跟着向后倾斜下去。窄地下面是一个陡坎,一直延伸到虎腰处的大牛圈。黄牛像一座山,稀里哗啦倒了下去。牛是拴着的,鼻子不堪重负,豁掉了,只留系在树桩上的一截牛蝇。
"牛一翻身,百天归命。"村里人都知道这句话。
黄牛从虎头滚落到虎腰,不知翻转了多少回身,归了多少回命了。
听到这声音,全家惊呆了。我们都跑了出来。出事了!母亲从磨房,父亲从一块苞谷田里,我们几个小娃娃从抓石子的游戏中。
看到这阵势,我愣住了。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儿。那时,牛的地位甚至高过人的地位。牛摔了就是人摔了。万一牛没了,田谁耕,磨谁推,牛的活路谁来干。要想办法。
父亲当即从村子里找来了兽医,熬制了牛药。我们几个孩子也出力,跑到了方家山村,那里住着几个舅舅,我们找来了几个表哥,他们二十来岁,年轻力壮,加上在五队请来了几个小伙子,一咬牙,硬是合力把黄牛给抬回了大牛圈,总不能在野地养伤。
牛卧在大牛圈的一个角落里,开始喂母亲熬好的药。我们帮忙,把牛嘴掰开,用筷子,竹片撑着,父亲把灌在竹筒里的药往牛嘴里倒。牛浑身是伤,鼻子豁掉。它摇头,撇嘴,咬断筷子,不喝。
父亲无奈,腾一只手,给它梳身子。父亲,我从没见你这么温和过。
母亲在一旁流着泪,用手扇着风,给它驱赶聚在伤口上的蚊子。
妹妹最小,着急地哭开了。
牛啊,干不完重活儿累活儿的牛啊,你真的会"百天归命"吗。
你这一去,是要给谁去做牛做马呢。
父亲提了提神,决定再次尝试。这回,父亲举起竹筒,全然不顾身边的我们,也不要我们帮忙,只顾对牛说话。
"畜生啊~~喝药哦~~你喝了我家新房建在一块很像老虎的石头上这是风水宝地吗,我们还是要你哟~~"
"畜生啊~~喝药哦~~你不喝,阎王可就要你哟~~"
放平时,父亲像唱歌又像哭的话,会让我们笑坏肚子。严肃的父亲,对一头牛,说温情的话,唱绵软的歌,我们很惊奇。他对别人,对我们从没这样说过话,唱过歌。他一生唯一唱过的这首歌,调子软得像根柳树条子,又像四月天里村子上空顺风飘的云。
妹还在哭。
母亲开始在哭。
我想哭。
一旁那只站在牛圈石包上的羊,呆望着睡在脚地上的牛,眼向下垂着,也想哭。
大牛圈想哭。
黄牛微闭着眼,顺着父亲唱的两句话,赶了两趟路。它只能用眼赶路了。腿已断了。
它向回赶,回望与我们一起生活的这十来年(它是头老牛了)。它握住了父亲点到即止的软条子,捉住了母亲推一会磨让它歇息一下像它母亲的一双眼。
它向前赶,来到了又一世。摆在眼前的,是无边的青草。当然有更大更重的石磨石磙,更宽更广的等待一头牛的田。
它赶路,它回来。
它突然使了一股劲儿,仰起头,睁开眼。长长的牛睫毛枯萎掉落,如大旱后的秧苗。眼角糊满了眼屎。蚊子趁它打开眼,停在里面,贪心地吸两口。好痒,它闭一下眼,蚊子又灵巧闪开。就这样,一睁一闭,几粒泪滚落出来,大得像几颗胡豆,浑浊得像沟里发的水。
胡豆熟成了墨黑的荚子。性急的,炸开了壳儿,像老婆婆空荡荡嘴里的几颗牙。胡豆年轻时漂亮,老了丑。这是胡豆的事,没谁管得了。我们不嫌丑,扯回来,摊稻场上,晒半天太阳。下午,胡豆荚儿晒得酥酥的。噼噼啪啪,爆响一稻场阳光。
接下来,就是黄牛的事了。
在这个共同的家里,每个人,每个牲口,谁都有该做的事。时间到了,事来了,谁也不偷懒,不推脱,也从没想过推脱。一切从朝阳观来,也不打算到别处去。该做啥子就做啥子,躲也躲不过。也没想过躲。天该晴了,太阳就在村子上空晃一晃。该下雨了,几坨黑云就屋顶推一推,搡一搡,挤几点雨做个样子。各负责各的事儿嘛。别说这些,连稻场坎外那窝小黄蚂蚁也懂这个道理,直到我后来离开那天,它们仍在这耕作、扬场、打猎、恩爱。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。不知过了多少代的蚂蚁,这又是第几代蚂蚁。
胡豆晒好了。
黄牛拉着石磙,父亲赶着黄牛,一颗颗胡豆碾了出来。一切是慢腾腾进行的。不需要有多快。那样的下午,父亲、黄牛、胡豆有的是时间。
又有几颗胡豆从黄牛眼里滚出,发出啪啪声。这声音,只有父亲听得见。奇迹发生了。黄牛听了父亲的歌。信了父亲的话。赶了两趟路。它咕噜一声,一仰脖,把竹筒里的药全喝下了。又喝了几竹筒。乖巧得像个娃子,我们中间的某个娃子。
以后几天喂药,我们回避开了。不需大动干戈劳我们帮忙。我们帮不了忙。我们知趣。牛只听父亲的歌,信他的话。父亲一人,在大牛圈里,不知又换了些什么话,唱了些啥子歌。反正每次的药喝得一滴不剩。
这些话,这些歌,这些药,成了父亲与黄牛间的秘密。我们永不知道、也不打算知道的秘密。
第四节
黄牛的状况恶化下去,连平常最喜吃的苞谷棒子壳儿也不吃了。平常,母亲舍不得,总是留待冬天大雪封山,没口青草时才拿出来给它打牙祭。
母亲急得不成样子,又拿出人吃的苞谷面,熬成粥,盛在脸盆里,端在它跟前。活一辈子,黄牛第一次吃人吃的东西。
母亲看到的是:它迷迷糊糊地睡着,抬眼皮,望母亲一眼。再抬眼皮,望一眼。
想吃。
站不起来了。
"畜生啊~~吃吧。"
母亲学父亲腔调,唱给黄牛听。她担心,她不唱上这一声,黄牛信不过她。怕吃后鼻子上挨一条子。那回,推石磨时,它舌头在磨盘上卷了一口苞谷面,给过它一条子。不轻不重的一条子。力度是刚好让它记得这是人吃的东西的力度。这样就行了。
也是在这个共同的家里,各有各的吃的。狗、猫、猪、羊、鸡、小到老鼠、一只夜蚊子,都不能越界吃别人的。只不过牛和小娃娃一样,有时要在条子下,才明白这个道理。
站不起来就睡着吃。
都喂到嘴边了。
这粥怎么吃呢,是像上次样用舌头卷,还是把嘴埋在里面吸。
黄牛受宠若惊,抬眼皮,松眼皮间,没了主意。
全懂了。母亲看懂了它的心思,认定它就是她四个娃娃中的一个。她端高脸盆,递到牛嘴前,自个儿先撮上嘴,教它吸。黄牛想起来了,它小时吮过奶。它用了把力,开始吸起来。稀的汁儿很快吮完,留下稠的粥。母亲伸出舌头,教它卷。黄牛明白胡兴法:大牛圈第一节牛圈猪圈短篇小说,用把劲儿,席卷一空,脸盆舔得像家里那只黄狗的碗。
吃完,母亲还在脸盆盛上了盐水,让它漱口,解渴。
母亲调上桐油,给它一处处擦伤口。
母亲点上艾把子,每个傍晚时分,给它熏蚊子。
母亲把给过我们四个娃娃的东西,都给了它。
第五节
不知哪天开始,黄牛不那么爱喝粥了。后来干脆不吃不喝,更别说喝父亲的药了。父亲唱的"畜生歌",说的好话,全不管用了。它甚至懒得睁一次眼。像村里好多人,活到最后才明白活一世的道理:睁眼活不如闭眼死。
只有一个孩子看得明白。它分明在做一件事:一动不动地赶路。每天数趟的路。它很累。它紧闭的眼睛里,是蓊蓊郁郁的青草,茂盛得像它耕种过的秧田,像它年轻时某年的心事(它是一头母牛)。它还看到了它磨过的白花花的麦面,金黄的苞谷面。它要赶往下一个麦场,那里有给它安排好的活路,当然,少不了好吃的苞谷棒子壳儿、软软的条子、一头强健的牯牛、一个会唱歌的主人、一个懂它,惊人地洞悉了许多事物的八岁孩子……
它不怨母亲。不记仇母亲那天安排它推磨,拴它吃一口青草,就像它不记仇事发当时那连续的阴雨天气。这些事,能怪谁呢。
半夜我家新房建在一块很像老虎的石头上这是风水宝地吗,它把这些说给一个八岁娃娃后,就走了。
这天夜晚,我前后半夜睡得很死。半夜时分,却失声笑出了声。咯咯咯的。母亲从被窝惊起,摇我,我不醒。
第二天,一大早,他们照例第一眼去大牛圈看黄牛。它睡得死死的。父亲用他的大手去摇。
哪里摇得醒呢。
这些天里,它匆匆赶路,赶往另一个入口。它已于昨晚半夜抵达。我们醒来时,它已吃上第一口鲜草了。
黄牛从另一个入口走后,这个共同的家不完整了。像村里那口最大的堰塘豁开了一道口子,如一个没端牢的碗摔掉了一个缺口。后来,好多牲口也从这道口子走掉了,那只老黄狗、一年一头的年猪、年年都卖掉的好几只羊、只活了一个夏的蟑螂。就像每次杀猪后,我们心里会空落落的,为了弥补这种亏空,我们又养了新的牛、猪、羊。
新的是新的,走掉的,怎么也回不来了。
我的八岁,我八岁左右的那些年,从哪道口子走丢了。我找不回来。谁也找不回来。
我想到了多年后,父亲的这个入口,还有母亲的,大哥的……我们这个家所有的这个入口。
这不该是一个娃娃想的事,对不对。
第六节
我们请来了汪家垭的彭中伯。他是杀牲口的好把式,有一套好使的杀猪工具。我们总不能将一头牛像一只打碎的砂罐一样,往竹园里一扔了事。牛皮已不完整,摔下来时就挂破了,像父亲干活常穿的那身破衣裳。肉分给了附近的人,四队五队的。用篾穿成了小串儿,一户一串儿。
我们自己只留下一小串儿,丝毫不比别人多。母亲把它挂在灶屋楼顶的中梁上。中梁正对着我的床头。每天醒来,我看到一束阳光从亮瓦里穿透下来,恰好罩在这串牛肉干儿上,像谁伸出的一条金黄手臂,揽一个娃娃儿。
在那些无所事事的早晨,那头黄牛胡兴法:大牛圈第一节牛圈猪圈短篇小说,与我一道醒来。
父亲扛一把锄头,挖了一个深坑我家新房建在一块很像老虎的石头上这是风水宝地吗,把黄牛的骨头埋在了一个叫和尚坟的地头。和尚坟,据说是当年庙屋里死了和尚埋的坟。
这是一块好地,是我们的当家菜园。父亲几乎每天都要钻进去,干一阵活儿。活儿干得太频繁,有一天,把埋进去的牛骨头挖起来了。慢慢地,白花花的牛骨头接二连三冒出。
父亲不仅种庄稼,也种骨头。他小心捡起,看看,不吱一声,依样埋在了地头。
我十二岁那年,母亲得了严重的风湿病,从此再也没有好起来。疼得厉害时,村里中医要她往中药里添牛骨头。牛力气最大,骨头最硬,熬出来的药自然强筋壮骨。
可在哪儿弄牛骨头呢。
父亲想到了地头的黄牛。
父亲扛上挖锄,从地头一根根掏骨头。每一锄头精确无误。他像清楚每棵庄稼样清楚每根骨头。
母亲病倒。四个娃娃要吃饭,要长大,要上学,要花钱。父亲的腰弯成了
一根骨头,一把锄头,一柄镰刀。
还是没效果。曾给它唱过歌,说过话,熬过粥的一截截骨头,治不好母亲的病。
母亲的病在骨头里。黄牛的奔跑不能到达,它赶不了这么远的路。
她一直病下去,病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。
不说了……大牛圈的故事至此结束,黄牛的赶路到此终结。
作者简介:胡兴法,男,70年代末人。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秭归作家协会秘书长。在《小说月刊》《北方文学》《骏马》《南方文学》《火花》《天池小小说》《躬耕》《青年作家》《中国校园文学》《做人与处世》《散文百家》《中外文艺》《工人日报》《羊城晚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湖北日报》《内蒙古日报》《西藏日报》《新西兰先驱报》《中国教师报》《南方日报》《检察文学》等三百余家报纸杂志发表文学作品150多万字(均可提供电子报刊或复印件)。作品获得各类奖项并入选多种文集。公开出版有散文集《风雨中的板车》等。参加2013年湖北省青年作家高研班学习并结业。现创办语蕊作文教育全国联盟机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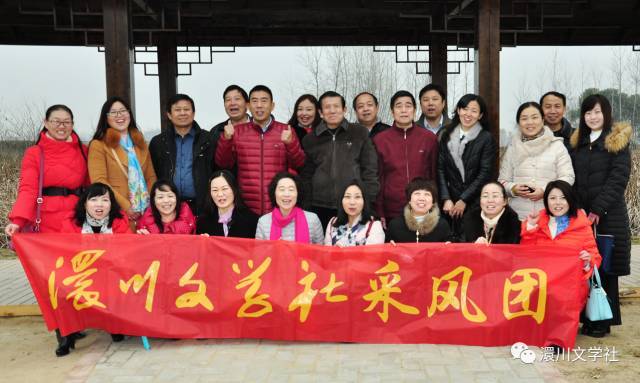
文学社坚持立足孝感,面向湖北,辐射全国,“不厚名家,不薄新人,搭建文学爱好者理想交流平台”的宗旨,网络了国际国内一大批作家,积极专注开展各项文学创作推广,得到管用和、李守义、赵金禾、任蒙等一批名家支持,他们欣然出任文学社顾问,并且形成了数十名名家与孝感作家组成的文学社委员团队,在宣传部、文联等职能部门的支持下,组织开展了抗洪救灾募捐、企业采风宣传、企业广告有奖征集、澴川文学创作大赛、周芳作品义务宣传推广销售等系列活动,推出澴川文学社微刊600余期,发文不完全统计近两千篇,已经出版《澴川文学》纸刊两期,推荐一名文学社成员加入了湖北省作家协会,一大批优秀稿件通过文学社推荐,在各级报刊刊发或者连载,不少作品被国家级名刊采用,有的作品还获得了全国奖项,澴川文学社一直是在艰难摸索中前行,能够取得一些成绩,得益于文学社全体成员的努力和各级领导的关心、鼓励和支持。
澴川文学社主编的《澴川文学》季刊,系湖北省新闻出版局批准,孝南区文联主管的合法刊物。内设刊首语、名家有约、经典看台、文心雕龙、沧浪诗话、梦溪笔谈、企业之窗、澴川文讯八大板块,文体不限,原创首发,欢迎投稿!
三、凡澴川文学社平台综合类型文字、澴川文学社主编文字,版权为主编拥有的,开通或关闭打赏随主编个人意愿。

管用和
澴川文学社主编
陈圣芳
